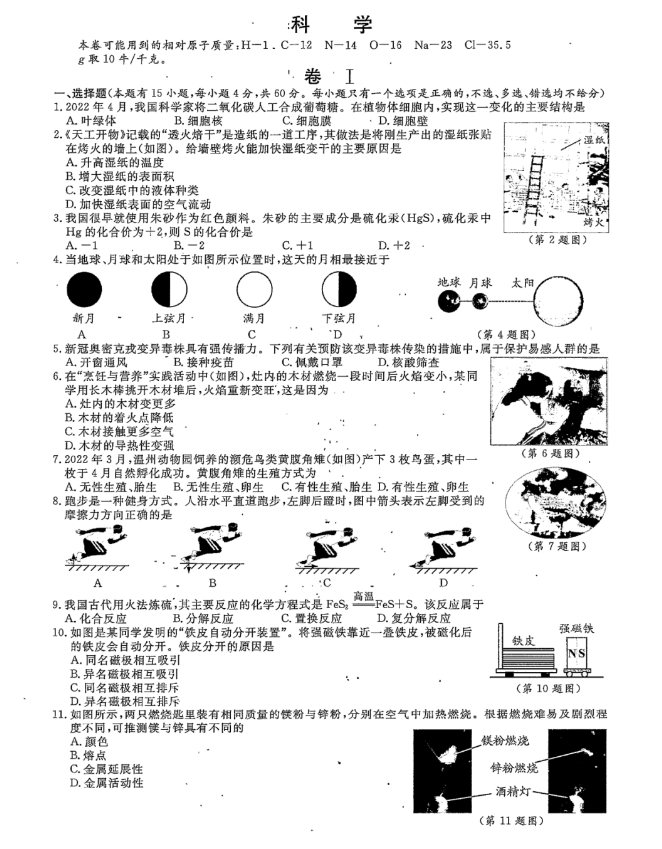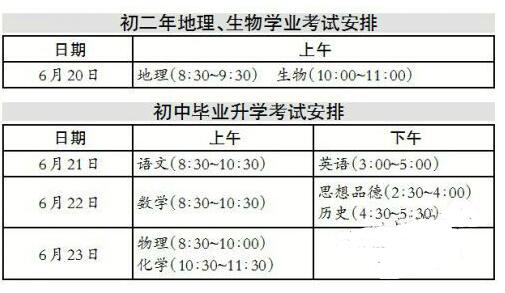中考,这个曾使很多人或悲或喜、或哭或笑的考试规范,已经在国内延续了近三十年了。作为一种选拔考试,它为国内教育事业的进步,为社会的进步,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但因为国内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贫乏,这个牵动过千家万户的考试,却给很多学生和父母留下了太多的回忆。作为一个亲历中考达十年之久的教师,我目睹和感受了学生和父母太多太多的焦虑、等待、喜悦和哀愁。细细回味,足可以成书。
不平等条件下的角逐
几乎在高考考试规范恢复的同时,国内的中学就恢复了选拔学生的考试。为了保证升学率,争夺生源就成了中考恢复将来所有学校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然而延续了近二十年的重点中学规范,在非常长一段时间却使这埸大战变成了不平等的角逐。未列入“重点”之列的学校曾戏称,省属重点是第一世界,市属重点是第二世界,未列入重点行列的学校则是第三世。这种黑色幽默不只道出很多学校的无奈和忿懑,而且也使这埸没硝烟的战争多少蒙上了悲剧色彩。
设置重点学校,是国家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实行的特殊政策;然而事隔二十年之后,大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能不面对如此的现实:这种方法在缓解十年动乱后出现的青黄不接、人才匮乏局面的同时,又给大家留下了很多遗憾。那看不见然而又实质存在的等级规范,曾使很多教师失去了工作的动力,使很多孩子对前途丧失了信心。这种规范曾使学校分为3、6、九等。中考后,当招生学校依省属重点、市属重点、市属骨干、市属一般、区属重点、区属普通的序列到招办录取学生的时候,省属重点和市属重点的最低分数线总是相差7、八十分之多;等而下之,区属学校能录到哪种学生,就不言而喻了。
这个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比赛,输赢清了解楚。“大家考上一个光荣,重点学校学生全部考上也是应该。”非重点学校的老师如是说。遗憾的是,高中三年,高分进入重点中学的学生,高考考试更不是个个金榜提名。名落孙出者,也不乏其人。这就让那些心不平、气不顺的非重点中学的老师们更没了积极性。那些生源最差的学校,教师怎么样教?学生怎么样学?校长怎么样管?哪一个父母会无怨无悔地把我们的孩子送到这类既难办好又没期望的学校去呢?“学不到常识,反而学了一身问题”,这是很多父母当时最担忧的。
很多学校的无奈之举
在初、高中脱钩以前,很多学校出于保护我们的利益,都采取过一些不成文的过激作法。譬如非第一志愿的学生不录;自己学校的初中毕业生不许考试报名其它学校的高中;省属重点学校落榜的考生,市属重点不收;本校的初中毕业生不听劝阻,考试报名外校落榜,一概不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类目前看来可笑而又不近情理的作法虽然年年遭到教育行政部门的批评和制止,但一些心高气傲的的校长,仍然我行我素,不愿更弦。这不只损害了学校的自己利益,而且也使这埸生源大战变得愈加惨烈。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市属重点中学。小升初考试没取消以前,学校每年招四个班200名中学生,但每年招生,考试报名的学生却超越500人。这也就是说,张榜之后,或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面临二次分配。尽管招生简章上黑纸白字写得清了解楚:填写志愿表时,考生可以在重点中学以外,再填报两个志愿,写上自己重点以外心仪的学校;但有的学校“非第一志愿不取”的原则,却使无数学生的第二道防线形同虚设。一旦被切到线外,就面临着被分到最差学校去的可能。我校附近有一所历史悠久、口牌很好的普通中学,小升初时,很多孩子都把该校作为第二志愿写到志愿表上。但录取时的潜规则,使很多孩子与该校失之交臂。几年过去了,考我校落榜的考生,几乎没几个被该校录取。尽管其中不乏考分较高的孩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校的高考考试升学率稳居市属重点学校的前列。缘由有3、很多有经验、有水平的老教师还工作在教学一线;学校生源好;初、高中还没脱钩。这第三点对大家尤为重要,由于大家的高中生源主要靠的是大家自己培养的学生,外校的考生,拔尖的学生要么去了一中,要么去了师大附中,考试报名我校的考生比大家我们的学生要略逊一筹。中考成绩下来,排在名次表前面的,是这类学生;三年将来高考考试,考上重点大学的,还是这类学生。这类学生几乎成了我校获胜的秘籍。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校的初中毕业生也日渐外流,这对我校的高中招生导致了不小的威胁。开始是3、五个,后来进步到一走就是十几个。稳定后方,就成了主管招生工作的主任每年招生时的一项尤为重要的工作。开会、谈话、家访、许诺,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名也报了,准考证也领了,可是一到考试的那一天,很多考埸的座位都是空的。原来这类学生全跑到一中和师大附中去考试了。行文至此,我不由笑了。我怀着一种很难言状的心情想起了当年学生和我开的这个小小的玩笑。我理解学生当年的这种做法,其实师生双方都是一种无奈。考试结果出来,这类流失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都考上了省属重点,而且考试成绩都很好。一个缘由是他们都是一些很出色的学生;另一个缘由是,他们了解,这种选择只能背水一战,一旦考试失误,要想回到母校,会比登天还难。
不好的风气使很多家庭雪上加霜
招生文件明文规定:招生学校不能超计划招生;录取时须按学生志愿依次录取。这也就是说,学生第一志愿没录,去第二志愿学校,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各种人为原因使招办每年在坚持原则的首要条件下,不能不灵活处置遇见的各种问题。这就使一些幕后买卖,堂而皇之地合法化了。记得有一年录取时,有一个第一志愿考试报名普通学校的落榜考生,考分非常低,学校也要纳入计划录取,主管校长顶住不录。电话打过去,他们毫不松口,一直顶到下班,最后不能不以妥协告终。
中考之惨烈,感受最深的不是那些校长们,而是许很多多被切到线外的考生父母。不能超计划招生是多年不变的一条铁定的纪律。考生一旦被切到线外,很多家庭顿时天塌地陷,宛若大难临头。有方法的父母早在中考试前就找好了退路;而那些无权、无势、无方法、无背景的父母,此时只能到处求情,终日以泪洗面。记得一次一个父母说到伤心处,几乎跪地相求。目睹此情,叫人心酸。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只能同情,但无力相助。
自古以来,教师以育人为本,安贫乐道是很多人的操守。但自从生源大战的烽烟腾空而起,校园不再平静,校长们陷入了重围。父母、熟人、上司、至交,弄得校长们不能安生。明智者闭门谢客,避之又避;但更多的校长们是陷入其中不可以自拔。于是乎每年盛夏,条子满天飞,电话响不停,校长办公室人出人进,学校门前车来车往,就成了很多学校最独特的一道风景。年复一年,很多手握招生大权的校长,屡见不鲜,乐此不疲,使这本不应该发生的一幕,年年在学校重演。
校长们的无奈,不身临其境,是很难领会的。但这种无奈带给学校的负面影响却是灾难性的,每当开学,定额45人的高中教室,总是人满为患,少则60多人,多则竟达70人,其中不少学生考分非常低。班额大,教师负担加重;学生程度不齐,老师很难施教。前多年,有些重点学校教学水平紧急下滑,不可以说这不是缘由之一。进入重点的线外生,无论分高分低,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其中的艰辛,只有父母心知肚明。
回忆后的沉重深思
多少年来,这类往事深埋心底,老师、学生、父母时时勾起我的回忆。本文涉及很多往昔不为人知的秘密,笔者只是想借“西部情”以抒胸臆,让激烈角逐中的学生、父母和教育同仁对比借鉴 ,能从中吸取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教育事业如火如荼,大家对教育看重的程度已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大家面对的现实是,国内教育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难以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其中有政策上的失误,也有很多人为的原因。本文所列很多遗憾,就是这一结论的佐证。
“目前考一所好的高中比考一所重点大学都难”,这是大家常见的怎么看。只须你到中考咨询会上看一看到处攒动的人头,校长们疲惫的面容,记者时时闪动的身影,父母凝重而又焦虑的目光,你就会了解这埸角逐有多激烈。上一所好高中,这是很多学生和父母的理想;最大限度地优化我们的生源,也是很多校长的心愿。但这否是能每人如愿呢?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有时我突发奇想,假如叫人们心目中的好学校和普通学校置换身份,让好学校的老师去教普通学校的学生,让普通学校的老师去教好学校的学生,结果将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前者就肯定战果辉煌,后者就一败涂地呢?对此,大家会不假思索地做出一至的判断。做如此的假设是想让父母不要低估了普通学校的办学能力。名牌学校靠的是优质的教育资源来吸引学生;而普通学校靠的是对事业的忠诚和拼搏精神来求得社会的承认。会宁等很多办学条件远不如都市学校的地县中学如此做了,而且做得很漂亮,亦很成功。
最后告诫父母,不要给孩子施加太大的重压。名牌,学生要争取;但孩子一旦考试失误,应退而求第二,未必非要砸锅卖铁,挤进名牌。名牌的优势不容置疑;但重点中学工作的历程告诉我,父母心目的好学校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样样都尽如人意。师资力量不足,学校疏于管理,教师忙于家教,这在一些学校并不鲜见。十多年前,每当秋天开学,是我最发愁的时候,教学班级增加,教学骨干锐减,排课左右为难,到今天记忆犹新。
“6月考孩子;7月考老子(跑关系);8月考票子(缴费)”这首新民谣形象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现实。又是一年鏖战时。愿校长们洁身自爱,不要让父母背上沉重包袱之后,再雪上加霜。